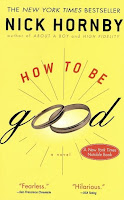 在網路書店遊覽時發現上個禮拜才看完的 How to be Good 夏天要出中文版了。雖然說書還沒出就趕來打槍實在不是件厚道的事﹐但這本 Nick Hornby 2001 年出版的書實在不能算是水準之上。Nick Hornby 的書在台灣最近才翻譯完成﹐不過因為 High Fidelity 和 About a Boy 兩部作品被拍成電影﹐他早就是當代英國作家裡出國比賽叫好叫座的寫手。從談論足球生活的 Fever Pitch﹐一邊聊愛情一邊聊音樂的 High Fidelity﹐到三十歲沒有經濟困擾、家庭壓力以致呈現社會真空狀態的 About a Boy﹐Hornby 的主角總是些看似輕鬆﹐想認真起來又極為混亂的老男孩。因為和大眾文化貼的很近﹐Hornby 的書往往配合著特定年代﹐和那個年代裡的某個典型。時間過去﹐這典型慢慢老了﹐心境還想繼續做聽音樂看足球的少年﹐社會卻一件一件貼上來﹐主角的苦惱越來越多﹐關心的事情也慢慢轉變﹐音樂和足球慢慢變成興趣﹐到本書則幾乎消失。
在網路書店遊覽時發現上個禮拜才看完的 How to be Good 夏天要出中文版了。雖然說書還沒出就趕來打槍實在不是件厚道的事﹐但這本 Nick Hornby 2001 年出版的書實在不能算是水準之上。Nick Hornby 的書在台灣最近才翻譯完成﹐不過因為 High Fidelity 和 About a Boy 兩部作品被拍成電影﹐他早就是當代英國作家裡出國比賽叫好叫座的寫手。從談論足球生活的 Fever Pitch﹐一邊聊愛情一邊聊音樂的 High Fidelity﹐到三十歲沒有經濟困擾、家庭壓力以致呈現社會真空狀態的 About a Boy﹐Hornby 的主角總是些看似輕鬆﹐想認真起來又極為混亂的老男孩。因為和大眾文化貼的很近﹐Hornby 的書往往配合著特定年代﹐和那個年代裡的某個典型。時間過去﹐這典型慢慢老了﹐心境還想繼續做聽音樂看足球的少年﹐社會卻一件一件貼上來﹐主角的苦惱越來越多﹐關心的事情也慢慢轉變﹐音樂和足球慢慢變成興趣﹐到本書則幾乎消失。
這本書特別的地方是觀點從男人變成了女人。女主角的職業是家庭醫生﹐做好所有社會認同的”好事“﹐丈夫是 SOHO 型的文字工作者﹐唯一穩定的收入來自社區報﹐每週一次在上面尖酸刻薄地大發牢騷。女主角時常希望丈夫變”好“﹐於是災難來臨﹕她的心願實現了。
此書仍然帶著極大的自傳(或是自省)風格﹐冷眼處理英國典型文化中產的生活。他們投給 Liberal﹐做資源回收﹐反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和貧窮。住在倫敦外圈的小房子﹐撫養子女﹐偶爾找保姆來看看孩子﹐去劇場區看戲。週末和朋友聚餐﹐一同諷刺看不過眼的政客、歌手﹐及所有他們看不起的人﹐確定彼此心照不宣﹐再心滿意足的回去。其典型和英國男人下班後一同去喝啤酒看球一樣經典﹐只是單位從“個人”變成了“家庭”。可能女性觀點畢竟是第一次使用﹐加上要自我反省總有些難堪意味﹐不似之前寫來這樣流暢。前面半本的大改變敘述完以後﹐後半像作者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只有亂七八糟草草了事﹐有點虎頭蛇尾。整本書除了一些戲謔的小段以外(列出他丈夫不喜歡的公眾人物就整整去了一頁)﹐最出色的是神來之筆的最後一段﹐描寫洪水殺進房子﹐父親爬上屋外清排水管﹐全家一起合作的片刻﹕
He's wearing jeans, and Tom and I grap hold of one back pocket each in an attempt to anchor him, while Molly in turn hangs on to us, purposelessly but sweetly. My family, I think, just that. And then, I can do this. I can live this life. I can, I can. It's the spark I want to cherish, a splutter of life in the flat battery; but just at the wrong moment I catch a glimpse of the night sky behind David, and I can see that there's nothing out there at all.
我和湯姆一人一邊抓著他牛仔褲後面的口袋﹐試著把他固定住﹐茉莉則在後面抓著我們﹐小手沒什麼實際作用但甜上心頭。我的家庭﹐我想﹐我的家。然後﹐我可以的。我可以這樣生活下去﹐我可以﹐我可以。我想珍惜這瞬間的火光﹐將盡電池的最後噴發﹔但就在這天殺時刻我瞥見大衛背後的夜空﹐那裡什麼也沒有。
Hornby 本身住在倫敦北郊﹐2001 年他編了一本書叫 Speaking with the Angel﹐所有收入捐給一所自閉兒特殊學校﹐他兒子就在那裡讀書。印象最深刻的是數火車 Transpotting 作者 Irvine Welsh 的短篇故事 Catholic Guilt﹐死去主人公的靈魂得到的處罰是“不斷夾進他人的性生活也就是不斷趴在受者身上被不斷地幹屁眼”﹕想到這裡或許我還是再去多看本 Welsh 。
2008/06/30
如何是好 How to be Good
2008/06/29
而且自閉。
預備同遊的父親表示若陳無法在英國取得俄羅斯簽證,屆時便只能在船上看《罪與罰》,情何以堪。我安慰父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陳最喜歡的作家,書裡主人公坐牢後女主角搬到監獄外面守候男主角。父親說那倒是符合情節,到時候我便可以在聖彼得堡港邊守候辦不到簽證下不了船的陳:沈家的語言邏輯。
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日前刊文,開列多位英國著名作家的“欲燒書單”,不免令天下愛書人瞠目,其中既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弗吉尼亞‧伍爾芙、DH.勞倫斯這樣的過往大師,亦包括多麗絲‧萊辛、薩爾曼‧拉什迪、伊恩‧麥克尤恩等一眾當代名家。
據報導,《星期日泰晤士報》小說版主編彼得‧坎普一馬當先,稱“陀思妥耶夫斯基總是將我擊潰”。他從未讀完過《白癡》,而陀氏的歇斯底里、臆想和狂熱傳染 了他,“幾乎要弄死我,就像害了一場病”。專欄作家西蒙‧詹金斯也選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說他有次度假時帶了《罪與罰》,結果把它丟進了游泳池,“每一頁都好像算計著,要把你弄得萬念俱灰……我確信,要是周末想去西伯利亞自殺的話,它倒是挺合適。”頭牌暢銷推理小說家伊恩‧蘭金則挑出了拉什迪的《午夜的孩 子》,並自述好幾次讀它,都沒挺過前10頁。他少年時很喜歡托爾金的《霍比特人》,但讀了30來頁的《魔戒》就不得不放棄。但他最恨的是諾曼‧梅勒的《古 夜》(Ancient Evenings),上大學時因為主修美國文學,便硬著頭皮看到600頁,最終被書裡的法老和變態性事弄得作嘔。“他(指梅勒)給 我上了一課,那便是:讀不完某本書也沒什麼大不了的。”評論家和小說家克里斯托弗‧哈特選了勞倫斯的《聖馬爾》(St Mawr),又補充道:“確切地說,是勞倫斯的所有作品。”——因為他缺乏幽默感,實在無趣。作家DJ.泰勒也將白眼給了勞倫斯,他小時候偷看爺爺珍藏的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其中的性描寫逗得他咯咯直笑。他說,“太做作了。”此外,《星期日泰晤士報》文學主編蘇珊娜‧赫伯特認為,多麗絲‧萊辛的《金色筆記》過長,過時,而且自閉。
《東方早報》2008-06-262008/06/27
Burning Cities

San Gimignano 的高塔還留下14座﹐像電影 The Ninth Gate 最後惡魔住的山頂﹐誰到那裡都會畫畫。小城教堂裡的壁畫輝煌﹐描寫地獄景象異常嚴厲﹐擋不住敵人入侵﹐於是時間停擺﹐像龐貝火山爆發。就留在中世紀。
Siena 曾經是寡頭政治的模範﹐象徵九人政府的大廣場﹐人們沿著坡度躺地上﹐紅磚做的海灘。
羅馬熱的像尼洛還在﹐窗子打開那大天井看得到誰家晒衣服﹐誰家床前讀書﹐誰家一群人聚廚房裡一起看那臺小電視歡呼。意大利踢西班牙﹐延長了兩次時間還踢不出所以然來﹐十二碼輪班罰球﹐罰的是球門。對方擋下兩球﹐電視裡歡呼。下半夜﹐整個城市像死了一樣安靜。
梵蒂崗金碧輝煌。是歷代教皇粗暴地請藝術家留下功勣的成果﹐和米開朗基羅比脾氣大﹐比不過後者長命﹐一路活到八十九﹐活活伺候三四任教皇﹐呼來喚去。教宗威脅將他從鷹架上扔下﹐他受了門房的氣半夜把家當全賣給猶太人騎馬就出城去。還得他三番五次寫信拜訪將他請回來。像情侶賭氣。
Tuscany 粉妝玉琢﹐羅馬堆金砌玉。教廷帶來的嘆為觀止多過感動﹐遊客湧入目睹教廷腐敗痕跡﹐嘖嘖稱奇。神又比國王高一點﹐砍不了祂的頭﹐可以轉性懷疑。
藝術的高點是用權力累積來的。樹頂的一顆星放上去以後﹐聖誕也結束了。
2008/06/17
午後之死
 看完 Sylvia Beach 自傳後去圖書館把她兩位朋友的書借了回來,才發覺過去對海明威實在不太公平。大概是童年某個下午在別人書架上看完那小小一本的老人與海後就對他失去興趣,以至於高中在班上讀他半自傳的 A Farewell to Arms (戰地春夢)也沒多費心。一直到這次讀到 Death in the Afternoon 才平反他。有些作家其實看翻譯也沒有什麼差別,有些作家卻一定要看原文才能感受到筆下的俐落。某些兒時看過卻毫無感覺的作品看了原文以後才真正被打動(自然,看了原文還是無動於衷的也有)最明顯的大概是麥田補手:大概因為咒罵的話翻譯以後總是不夠力。
看完 Sylvia Beach 自傳後去圖書館把她兩位朋友的書借了回來,才發覺過去對海明威實在不太公平。大概是童年某個下午在別人書架上看完那小小一本的老人與海後就對他失去興趣,以至於高中在班上讀他半自傳的 A Farewell to Arms (戰地春夢)也沒多費心。一直到這次讀到 Death in the Afternoon 才平反他。有些作家其實看翻譯也沒有什麼差別,有些作家卻一定要看原文才能感受到筆下的俐落。某些兒時看過卻毫無感覺的作品看了原文以後才真正被打動(自然,看了原文還是無動於衷的也有)最明顯的大概是麥田補手:大概因為咒罵的話翻譯以後總是不夠力。
幸好 Death in the Afternoon 似乎還沒有翻譯。親手嘗試翻譯後可以理解為什麼。海明威最出名的一手在記者生涯培養出來的“電報型文筆”,翻譯以後還是冗長,可惜了原來的簡潔。Death in the Afternoon 鉅細靡遺地描寫西班牙鬥牛的歷史,每年進行的時間地點,座位的差別,買票的方式...... 鬥牛士的培養過程,歷史上出名鬥牛士的歷史,生長背景和故事......。三百頁後還有歷史照片,與鬥牛有關的西班牙生字表,最後附上三歲到三十歲的美國人觀賞鬥牛後的反應記錄,及美國籍鬥牛士 Sidney Franklin 小傳。除了介紹鬥牛外,這書更像以鬥牛為中心的西班牙文化深談,旅遊報告,和人類學論文。邊看著邊有開車上路往西班牙去的衝動。
鬥牛一直是一件危險性很高的活動,出名鬥牛士時常死在場上。海明威認為鬥牛是另一種悲劇的形式,牛是在最後一定得死的悲劇英雄。事實上,在十六世紀教宗下令禁止前,鬥牛可以反覆上場,累積經驗的鬥牛極難對付,要確定能擊中目標才會採取攻勢。當時的死亡機率自然比現在高出許多。一直到海明威在的年代,仍然有貧窮的省份在非專業的市集鬥牛裡重覆使用“選手”,造成許多死傷。一頭鬥牛便有奪取十六條人命和六十人受傷的記錄。死去的六十人裡包括一位十四歲的吉普賽男孩。他的兩位兄姐跟蹤這位殺人兇牛長達兩年之久,直到非法鬥牛場被解散,牛主人將牛賣到屠宰場。獲得屠宰場同意後兩人先剜去籠中牛眼,在窟窿裡吐口水,再以小刀將牛背脊割開,取下牛睪丸,在風塵僕僕的路旁生起一團小火,吃掉烘烤過後的牛睪丸後,轉身離開背後的屠宰場,沿著路走,一路走出城外。
2008/06/13
法文真是愛情的語言麼﹖
刻板印象“可以是件壞事﹐不過一旦”刻板印象“已經造成﹐大方適應倒可以有許多好處。不管你是挑剔的法國女人﹐出身低下於是言辭骯髒的英國廚師﹐還是娘娘腔生活紊亂的同性戀﹐一旦人們”認知“你是如此﹐你便能暢行無阻在他們的刻板印象中。多麼刻薄、口不擇言、粗暴無禮都能自然成為一種趣味。了解各式各樣的“刻板印象”是了解英式幽默的一大部份。生在都柏林的主持人 Graham Norton 就是玩弄刻板印象的高手。公開男同志身份的他在螢幕上完全生冷不忌﹐比 Friday Night Project 的 Alan Carr (也是一個有名的電視同志主持人) 還要厲害幾倍。
The Graham Norton Show 這禮拜請來朱麗葉畢諾許以及在電視上罵髒話出名英國名廚的 Gordan Ramsey (他自己的電視節目叫 "The F word")﹐三人大開法國人玩笑。搞得 Binoche 只能說”我不知道這個節目這么蠢啊。“
試試就知﹕
法國藝術電影﹐導演﹐還有”法文是愛情的語言“
French Art house cinema, Monsieur Director, and "French is a language of Love."
同性戀﹐法國女人和一個英國廚師
Homosexual, French woman and a Fucking Chef.
Does everything really sound better in French?
There are many advantages if you act unapologetically towards stereotype: whether you are a mademoiselle, chauvinist chef with foul language, or gay - with pride, It seems like since you're "in the role," you can be easily forgiven for what you were being accusing for. You can be mean, ask rude question, or act like a woman as much as you like. They all become part of the humor. People loves to be confirmed. Since you're confirming their preconception, serving the verdict can never be wrong. Nobody likes to be scouted, but you won't be offended when Gordan Ramsey ask you to "Fuck Off My Kitchen." Well, if you know him, that is.
French Art house cinema, Monsieur Director, and "French is a language of Love."
Homosexual, French woman and a Fucking Chef.
兩城一館

總是有些地方讓你下車就想離開 - 尤其是銅像也算一種景點的時候。
哥德在這裡讀了很久的書﹐浮士德一幕就在他時常去的此處酒館﹔巴哈在這裡的大教堂彈過琴 - 這兩人足跡遍布德國上下﹐到處都拿他倆做招牌鴨。萊比錫是老交易所﹐貿易匯點﹐那教堂柱很革新地從未見過﹐像糖果做的巨大粉色長青植物。
Weimar
“偷書賊”裡提到納粹在街上燒非德國書的歷史﹐作者認為德國人愛燒成性是原因之一﹐這熱情至今未減。Weimar (在我看來) 最重要的 Duchess Anna Amalia Library 2004年九月的火災﹐燒掉的五萬套書中﹐一萬兩千五百套孤本從此絕世。1534年的路德聖經﹐洪堡的手稿﹐浮士德... 只是救回來的一部分﹐不敢想像救不回來的都是什麼東西。下午洛可可式的橢圓形主堂不開放﹐樓下展覽早期歐洲印刷品﹔自古騰堡開始一百年﹐活版印刷的技術到歐洲各城﹐各個城市各自發展印刷術。相比之下﹐自動灑水系統的發展就慢多了。
十九世紀初威瑪不過六千人口﹐寡婦 Anna Amalia 愛書也愛作者﹐此間頓時變成文化小鎮。巴哈的 Ava Maria 在這裡寫成﹐哥德在圖書館做了35年的圖書館員﹐下班後和席勒去聊天。 畫家Cranach、鋼琴家 Liszt 長年在此﹐瘋了的尼採也在這裡渡過最後的七年。
我想我還得回去。
Holocaust 的描述比想像中少﹐畢竟是猶太博物館不是 holocaust museum﹐從誤傳的程度上看來﹐它們兩者差不多被劃上等號。展覽從 Diaspora 一詞開始談猶太人的”以外“﹐談他們在歐洲居留與被迫害的歷史﹐他們的遷徙和文化。建築和展覽都很出名﹐資料很多﹐不過沒有為了爭取以色列國土需要犧牲多少人命的資料。
也或許﹐土地本來就得這樣討來﹕買來﹐要來﹐戰來﹐以苦難歷史作籌碼爭取來。
你很難不關注猶太族群。猶太博物館如雨後春筍在世界各城市建立﹐以色列永遠是中東的頭條。它聲音很大﹐曝光的機率也大。因為一樣的原因﹐你也很難關注它。你知道他們有故事﹐集體的屠殺其來有因﹐只是沒解釋殘忍的歷史如何造成今日他們對他人的殘忍。他們的暴力大程度地被正常化了﹐理所當然的事情是不用蓋博物館解釋的。
Museum is a process of framing. 框架以外﹐總是有沒說出來的。
2008/06/11
糖與炸

一個很男性的廣場。
必須奇異的說﹐意大利每個中世紀古城的 Piazza﹐法國教堂前的石板地﹐都沒有這個平坦水泥地好看。
Hackescher Markt
買了兩張蘇聯唱片﹐封面分別是舉著軍刀、整齊折腳的柔軟軍士﹐和彩色鉛筆畫的馬戲團。她買了一本很老的巴黎介紹。
”它太老了。“我說
”景點都是一樣的。“
也是。
又買了筆和筆芯。我拿在手上太重了﹐但他拿得起。彩色筆芯吐出來都是不同顏色﹐很方便。為了挑筆把手上的咖啡放在他攤子桌上﹐再拿起來已經冷了。
海克說﹐除了肉丸和一些燉物﹐沒有特殊的“柏林菜”。我們在下午吃巴伐利亞料理和啤酒。煎白腸陪酸菜、肝和肉絞在一起做成的脆肉片﹐像粉紅色的土司。

難看的書裡寫以前叫“列寧大街”﹐其實是“史達林大街”。 東德特地建的模範大道上﹐沿途的人民劇院﹐咖啡館﹐內容變了一點點﹐形象還是很好。復古又簇新地放在原來的地方。八十九尺寬大的街沒什麼人﹐老人一前一後慢慢的跺著﹔腳踏車從林蔭下溜過去﹐一個女子的狗就放在前面車籃裡﹐四腳朝天﹐還搞不清楚要掙扎的模樣。巨大的醫療用品店有兩層樓的玻璃落地窗﹐裡面的人除了一種站著一種坐著以外﹐無法分辨誰是塑膠人偶誰是員工。這下午唯一著急的是一個講手機的人﹐站在路中央的安全島上用力理論﹐焦急氣憤。
兩公里的街來來回回的走完。像一本好看的書﹐一塊難得的糖﹐放舌頭上﹐很享受地一絲一毫的得到它。
十二歲才在母親家鄉的廟口學會騎腳踏車﹐十四歲栽到熊溪公園的橋下﹐之後幾乎放棄騎車這項行為。下次可以在這裡試一下。
Charlottenburg
我住的這排建築很美﹐甚至有 Art Nouveau 式的大門﹐和對面幾乎只是不同長方形組合的統一公寓很不同。
“這裡是沒炸的﹐對面是炸了重建的。”檸檬小姐解釋到。
班雅明的童年就在這區渡過﹐還沒炸的時候。現在不用煤氣燈﹐但還是很昏暗。
我不明白他的散文好在哪裡。也可能桑塔格的前言 - 英俊二字 - 有所失格。她應知道男子以才為貌﹐免去這種繡上貼金的溢美讚詞。甚至應該感謝他其貌不揚﹐才帶來許多細微的絕望。一路空泛的建築領我走向更空泛的宮殿。冰冷的越王劍百般不願意地躺在這裡﹐身邊的玻璃櫃有破碗破盆、扭曲的陪葬物、千篇一律的大理石人像。潮濕的紀念品店賣著模擬原始人生活的明信片。
王宮沒有炸﹐人口太少﹐戰爭的陰謀者還沒想到摧毀別人文化遺產有什麼意義 (伊拉克的時候就想到了﹐第一天就炸了巴格達國家美術館)。只有痛恨階級的革命份子和獲勝的陰謀者可以將它們夷為平地﹐像 Metz 小城一樣﹐將軍銅像身後﹐一整片”人民的“乾巴巴草坪。
2008/06/09
柏林逐街又

想和巴黎香榭大道比擬﹐只是歷史易手多主﹐原本兩排檸檬樹拔了又種﹐種了又拔﹐連路底的 Brandenburger Tor 大門都曾被拿破侖拆了整組帶回巴黎過﹔拿破侖出門打仗前往往先開清單﹐到了比較不會手忙腳亂﹐這布藍登大門就在他 Shopping List 上﹐戰後才又搬回來。(想想納粹倒只愛折磨人﹐對搶人遺跡一向比不過拿破侖。) 東西柏林分開時這大門立在中央﹐算是兩邊人共同擁有的地標﹔遊客總要從東照到西﹐從西照到東﹐看看有什麼不一樣。來了數日﹐對東西柏林的刻板印象逐漸淡薄﹐西柏林也有灰暗地一式水泥大樓﹐東柏林也不乏整修過後的彩色漂亮露臺﹐最有“特色”的大概只剩東德留下來的巨大公共建築。這裡還見不著。
十九年了﹐東西柏林像一雙緊緊交握的手難分你我﹐市中心突兀地丟荒的圍牆週邊是中間的指縫。
Hackescher Markt - Museumsinsel
博物館島、洪堡大學都算東柏林﹐真不知道西柏林究竟得到了什麼 (戰前就有的百貨公司 KaDeWe 和皇家狩獵大花園 Tiergarten?) 感謝社會主義為柏林保留一點樸素。
Kreuzberg
說土耳其最大的城市在柏林有些誇張﹐應該是在柏林的十字山。檸檬小姐的土耳其同學推薦的餐廳果然不錯。上了菜才想起我和土耳其菜其實很熟。那年夏天做了兩個月的吧臺﹐被老闆運進台灣的兩位廚師手藝很好﹐但語言完全不通﹐主掌轉烤肉捲的那位喜歡上打工的少女﹐平日休息時興以利刀將她名字劃在手臂內側。熱情可見一般。

買來送檸檬小姐的書介紹了一些東柏林小街。雖然寫的實在不好﹐還是去看了看作者介紹的地方。週間下午仍有不少人悠閑地喝咖啡看書﹐果然是格瓦拉不愛官位愛叢林的信徒 - 不過是整理翻修乾淨的水泥叢林。太多標語弄得人頭痛﹐缺乏安全感的老青少年一向轉型困難。
週日牆公園有翻不完的破銅爛鐵﹐不少美國加拿大來的年輕人拿著小東西出售﹐口音好認。專賣瓷碗破盆的帳篷裡有一整箱整理好的投影片﹐盒子上寫著各個城市的名字。遲疑現在按了快門後這些影像未來命運如何。主人又命運如何。
晒得發暈。
書不好看﹐愧於贈人。聲稱身上留著革命的血可以發散一些浪漫的幻想﹐但那種血通常流得很快﹐且一般流在身體外面﹐而不是留在身上﹐作者要注意血栓。想認識德國還是看陳玉慧 龍應台會比較真實。“德國時間”一篇寫柏林省錢族﹐我有深刻感觸。二手市場一兩塊的衣服不算驚訝﹐但住家附近一套完整洋裝也不過五塊。我一身他人舊衣在這裡都變新的﹐沒有買進來也沒有賣出去的期待。
2008/06/08
柏林逐街

在 Luxembourg 的 Hostel 裡幾乎只有德文讀物﹐唯一一本英文小說是 Joseph Kanon 的 "The Good German"﹐帶去的 de Botton 很早就看完了﹐只有勉強自己看下去。小說描寫 1945的柏林﹐在盟軍大轟炸以後﹐做記者的男主角回到四年前來過的都市尋找情人 - 別人的老婆。當時盟軍在柏林佔領各自領地﹐是東西柏林形成的前因﹐冷戰的前奏。美國蘇聯共同做了贏家﹐各懷鬼胎﹐一面處理戰犯一面私下搶奪做炸彈的科學家。書本身不值一哂﹐不過可以想像一下書中描寫的戰後情境 - 夷為平地的 Potsdamer Platz 和充滿屍臭的巴黎街。現在是絕對沒有了。
劃開東西德的柏林圍牆倒了快二十年﹐遺跡還是遊客必看的地方。遊客可以從遺跡旁邊的亭子購買長得像早期手機的錄音說明﹐一路從北到南沿著越來越少的牆聽取歷史。那位創造 Objectum Sexual (戀物癖) 辭條的瑞典女性就是嫁給柏林圍牆﹐婚後冠夫姓為 Berliner-Mauer﹔可惜她丈夫日漸憔悴﹐還有人不斷摳它身體﹐在洪堡大學面前賣遺跡明信片。慘不過嫁給紐約雙子星大廈的柏林少女 Sandy。嫁給巴黎鐵塔的舊金山女兵最幸運﹐只需要擔心每日與它眉來眼去、鑽它跨下絡繹不絕的恩客﹐丈夫身邊自有佩戴機關槍的巴黎武警保護。
以豪華的 Sony Center 為中心的 Potsdamer Platz 只剩寥寥幾片瘦牆﹐不過身處市區中心﹐算是最多人關心的圍牆遺跡。站在牆邊的軍人身邊有幾個橡皮章﹐一看就知道是為收取小額費用與人合影還是蓋章紀念﹐於是沒什麼人靠近﹔那扮成軍人的老青年彎著背搓著手﹐極其討好地看著身邊遊客。神情像是戰敗後戰犯投誠一樣卑微。
柏林愛樂廳 Kammermusikaal 上趴著幾個工人﹐昨日剛著火的白色屋頂破了個黑洞﹐像有人硬是在上面擰熄了香煙。幸運的是﹐目前尚未有任何未亡人的消息。
2008/06/05
宅男啟示錄

有時在國外反而有機會看到這些國內的戲碼﹐而且場地通常比國內好得多。這次的票雖便宜﹐位置就在頭兩排﹐樂師百無聊賴的表情都看得清楚﹐尤其第二天坐第一排﹐頭兩場簡直震得耳膜發抖。想想古時大概就是這樣在茶館﹐一邊吃飯啃瓜子逗狗﹐一邊聽上面伶人唱戲﹐現在沒這機會了﹐只得正經八百地坐著﹐時候到了才可拍手叫好。
在牡丹亭之前﹐我自然是不知道國樂可以這麼美的。一般接觸國樂的地方﹐通常都是婚喪嫁娶﹐搭配輕解羅衫的場景比較多﹐再來﹐就只有兒時下午兩三點的京劇。香港作家李碧華幾部小說以戲子人生為背景﹐(其中一本“霸王別姬”後來改編成了電影)﹐是我小學時的讀物﹐從中可以窺得一些當時戲班子裡的生活。但舉凡中外談戲曲的電影﹐(外國的蝴蝶君﹐中國的霸王別姬﹐還是台灣的夜奔) 通常都醉翁之意不在酒地以早期的中國同性戀生活為主旨﹐戲曲只是寄情的遮掩。白先勇特別製作“青春版牡丹亭”﹐刪減劇碼﹐加強視覺﹐用年輕演員﹐大概就是為了拯救我們這代沒受過什麼戲曲洗禮﹐莎士比亞讀得元曲宋詞熟的一輩。
牡丹亭的作者湯顯祖和莎士比亞的年代差不多﹐和西廂記一樣都有鼓吹自由戀愛的意思。劇中女主角杜麗娘和白 面書生柳夢梅在夢中廝磨後﹐百尋不得犯上了相思病﹐死後埋在後院梅樹下。宅男柳夢梅則在春夢之後輾轉住進她因戰亂而荒廢的老家﹐先拾得她生前字畫﹐又像聊齋裡那些夜半讀書不是遇見狐仙就是小倩的書生一樣﹐以畫代人胡言亂語一番喚出麗娘魂魄﹔兩人夜裡數次幽會﹐麗娘才告解自己的鬼魂身份﹐請他快拿了鋤頭去掘她出來。終於起死回生。麗娘父親不信女兒轉生﹐要將柳夢梅下獄﹐最後一路鬧到皇上面前﹐才解決這在當時不被接受的 (現在恐怕也不容易) 私訂終身人鬼戀。
很難用現代標準界定牡丹亭的類型。它既是時代悲劇又是戀愛戲劇﹐還是起死回生、掘墓戀屍的科幻片﹔不但有戰爭裡諜對諜的愛國情節﹐又有鬧上法庭的“法外情”段落。第一天的“驚夢”在花園裡和陌生男子褪衣野合已夠教人臉紅心跳﹐昨夜和女主角父親交待掘墳細節和屍體磨磨蹭蹭更讓人汗毛直豎。怪不得白伯伯看了這麼幾年﹐還是不時驚嘆叫好!
青春版除了舞台和服裝都很講究外﹐男主角俊 (除了第二天入場前撞見他滿面油彩穿件白汗衫和樂師們抽煙以致形像有點破碎) 女主角氣質出眾 (演人嬌美演鬼懾魂)﹐連配角們都是一絕。無論是古靈精怪的丫頭春香﹐出場就令人絕倒的“石女”石道姑﹐還沒遭裁員的地獄判官﹐滿嘴胡話的金王使節﹐被錢收買了回去做海盜的搶金王和搶金娘娘﹐個個撐起場來都比男女主角還精彩﹐每晚三個小時坐下來﹐也不覺得膩﹐反而這下少了這高潮迭起的“連續劇”﹐有點不習慣。
如果“牡丹亭青春版”這名字仍然無法激起年輕人的興趣﹐可建議白伯伯直接叫“宅男啟示錄”﹐柳夢梅一介貧寒書生﹐家世差﹐身體弱不說﹐平日除了作詩弄詞做春夢外基本上沒什麼生活樂趣﹐最後竟然可以一舉考上狀元﹐還娶到了牆上掛著的“封面女郎”﹐實在“好羨煞人也”。
Sadler's Wells - The Peony Pavilion
Jun 3 to Jun 8 2008
脫光
陳均逢當年在法國讀書時並沒有像我這樣野腳﹐和法文拼命期間非常客氣地只去了阿姆斯特丹﹔春冬交接之際巴黎大罷課﹐他看著這些號稱很有思想但嚷嚷成份比較 多的學生﹐很疲倦地坐火車離開﹐從巴黎途經科隆一路坐火車到柏林。二月的柏林每日下雪﹐他幾乎是一到就病倒了﹐此後一個禮拜就躺在 Hostel 鐵床上發高燒﹐等友人帶回來的土耳其肉卷。稍稍好起來以後到沒什麼人的路上散步做復健﹐就著外面不怎麼亮的天光﹐看河上互相 推擠的冰塊。那風景不知道觸動了內在何處蠕動的地方﹐當下做出了離開歐洲的決定。
柏林的路很直﹐很大﹐每扇門都開的很高﹔不同與巴黎四分五裂的狹窄室內﹐也不同於倫敦一向低矮的門窗﹐從一整片大開的窗戶能知道室內的寬敞﹐這點也可從海克小姐家獲得證實。圍牆倒了快二十年﹐週邊仍然荒蕪﹐新的中央車站像外星船一樣落在空地中央﹐政府模仿巴黎夏日裝海灘的行徑﹐送了一些沙填滿空地﹐也真有人在上面打起沙灘排球來。沒人的地方就捲一捲迷你沙塵暴。大家灰頭土臉地走過去﹐或在水泥階梯上吃三明治。
無論早晨﹐中午﹐還是週末夜裡﹐無論它是電音首都還是歌德 龐克 金屬大本營﹐柏林一直很靜。不知是因為它的寬敞還是人們總低聲說話的緣故。在柏林見到一個人坐著的情況比別的城市多﹐他們一個人坐著喝咖啡 啤酒﹐看書看報﹐或什麼也不做﹔一個家庭坐在同一個桌上﹐各人看自己的書報抽自己的煙﹐時間到了就一起走去了﹐也很自然。
五月的冰早就融化完﹐樹葉也全都長出來了。我眼中的柏林自然和他見到的很不一樣。只是不必等到春暖花開﹐正在退冰的灰色柏林足夠成為他的一級城市 - 類似埃及是福婁拜的一級城市一樣 - 城市的內涵和我們對世界的期待和觀感產生共鳴﹐對某個城市的喜愛意味著對某些本質的喜愛。那可能是誠實﹐不做作﹐紀律和安靜。
柏林還是很靜。歷史裡它曾經這樣嚷嚷﹐如今弄出多大的聲響﹐也瞬間吸進背景去了。
有時它令我想起北京。
雖然這裡沒人光著膀子走在大街上﹐不過那些躺草地上晒太陽的人總是近乎脫光。
2008/06/03
古騰塔, 海克小姐

海克是檸檬小姐在演唱會上“搭訕”來的室友。當時檸檬小姐正準備從寄宿家庭搬出來﹐海克則因為朋友有事突然落單﹐兩個人相談甚歡﹐沒多久檸檬便搬進她的客房﹐開始同居生活。我先愛上她走廊上那拔天高的兩架大書櫃﹐再來是整個屋子的老傢具。它們都符合六呎高的海克水準﹐我確信住久身體會為適應而拔長﹐或是依達爾文設想變成長頸人。
海克小姐一頭金髮﹐是我遇見能把德文說的最溫柔的人。前東德來的她在電視臺工作﹐和許多媒體人一樣躲不過自然變成工作狂﹐下班也和同一群人續會的人生 - 至少十年﹐她說 - 前陣子她開始反思生活態度﹐最近大概是關鍵的轉折點。轉折前的陣痛是同時接兩個工作﹐時常凌晨三點出門製作六點的晨間節目﹐接著處理十點的第二個工作。週末晚上拿出足以烹煮五歲小孩的法國鋼鍋準備六人飲食﹐和父母老友在客廳共享燭光晚餐﹐討論哲學與教育﹐和電視上遺漏的報導﹔週三晚兩個友人來訪﹐在廚房聊天吃過茶點後﹐轉去客廳燒芳香精油做“沉默治療”。平日以廚餘茶渣堆肥﹐準備夏日蒔花弄草﹔週間空閑在客廳閱讀﹐或是拿鐵錘做木工。熱愛有機飲食﹐泡著豆類和透明海草的罐子裡是自己發酵的健康飲料。爐灶前有金木水火土飲食表﹐只加了粉紅色岩鹽和橄欖油的麵條勝過我在意大利各地的飲食經驗。
海克小姐是個身著便服的女超人。
書架上有法文英文西班牙文的學習手冊﹐和非洲歐洲亞洲的寂寞星球旅遊書。時間滿檔﹐卻不曾看她有絲毫匆忙﹐更無法想像她會想念巴塞隆納的西班牙男友想念到全身發抖還是手足無措 (不如再做幾個木椅吧)。廚房的水壺總是滿的﹐客廳的花總是新鮮的﹐海克小姐總是滿臉笑容﹐不忘和我說上幾句﹐以及最後的你早﹐你好﹐晚安﹐享受路程﹐有個好日!
同為肉身﹐我相信 (我希望) 海克小姐也有徬惶﹐軟弱﹐難受... 的時刻﹐也看過許多能把生活安排的風風火火﹐已臻化境的女強人﹔我沒見過的﹐是同時擁有緊湊人生和溫暖微笑的海克﹐自然﹐合適﹐“有機”。市面上的“獨立女性”總是有點奮力﹐有點勉力﹐有點刻意﹐有點千辛萬苦 特立獨行﹐有些前因後果 於是如今﹔一些姿態與口號﹐煮不熟的米心﹐燉不爛的橡皮筋。
祝福海克小姐的存在延續。
2008/06/02
行路

時間長的旅行除了有這種自然謀殺的好處以外﹐最重要的大概是改變每日習慣﹐再在路上養成新的規律。在意大利的時候﹐學會了用小鋼鍋煮牛奶﹐最後在加上磨卡壺煮好的濃縮咖啡﹐取代以前一杯牛奶撒上一匙即融咖啡去微波的懶人習慣。在家要改變嫌麻煩﹐但在路上看朋友這麼做了一個禮拜﹐就變成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也算是一種帶回家的”紀念品“。
在柏林的十天﹐生活基本上是這樣的﹕早上七點半起來和檸檬小姐吃早餐﹐送她出門上課﹐補眠以後看書等她下課一起去吃午餐﹐然後是下午的一貫行程﹕城市行軍。基本上是挑一個前一天晚上看好的區域﹐然後放腿狂走。一路走到晚上八九點左右﹐再慢慢的拖著腳步回家。頭幾天因為興奮﹐也不特別覺得累﹐只是一到家感覺黃暈暈的床特別舒服﹐躺了就沉下去一樣。後來身體養成習慣﹐天天時間到了就像上緊了發條﹐不走走就覺得全身不舒服。十天下來瘦了也黑了﹐不再是地下室養的那只白蛆。
回到倫敦﹐勤病未瘉﹐差別是柏林車不多﹐晚春太陽特別猛﹔倫敦車多﹐空氣不會好到哪裡去﹐但是擋了不少陽光﹐晒在身上也溫和一點。很難分辨哪個比較好。反正只要時間多﹐哪裡都是走得到的。陌生城市自然走起來比較有意思﹐不知道到世界各地馬拉松的莊曉陽有沒有這種差異感。
想想小時候和家人出遊﹐爸爸總被媽媽抱怨陸軍本色不改﹐每次都走得又急又快﹐讓有時胃痛有時腿痠的娘很吃不消。可能是我老子女兒當兒子養的成果顯現出來了﹐現在我這種不怎麼吃飯也不太睡覺的旅遊精神﹐也常讓身邊人不知道我是在度假還是在做鐵人三項。五月這兩次自己上路完全滿足了我的行軍慾望。說不定下次就特地為了走路﹐上路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