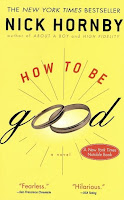 在網路書店遊覽時發現上個禮拜才看完的 How to be Good 夏天要出中文版了。雖然說書還沒出就趕來打槍實在不是件厚道的事﹐但這本 Nick Hornby 2001 年出版的書實在不能算是水準之上。Nick Hornby 的書在台灣最近才翻譯完成﹐不過因為 High Fidelity 和 About a Boy 兩部作品被拍成電影﹐他早就是當代英國作家裡出國比賽叫好叫座的寫手。從談論足球生活的 Fever Pitch﹐一邊聊愛情一邊聊音樂的 High Fidelity﹐到三十歲沒有經濟困擾、家庭壓力以致呈現社會真空狀態的 About a Boy﹐Hornby 的主角總是些看似輕鬆﹐想認真起來又極為混亂的老男孩。因為和大眾文化貼的很近﹐Hornby 的書往往配合著特定年代﹐和那個年代裡的某個典型。時間過去﹐這典型慢慢老了﹐心境還想繼續做聽音樂看足球的少年﹐社會卻一件一件貼上來﹐主角的苦惱越來越多﹐關心的事情也慢慢轉變﹐音樂和足球慢慢變成興趣﹐到本書則幾乎消失。
在網路書店遊覽時發現上個禮拜才看完的 How to be Good 夏天要出中文版了。雖然說書還沒出就趕來打槍實在不是件厚道的事﹐但這本 Nick Hornby 2001 年出版的書實在不能算是水準之上。Nick Hornby 的書在台灣最近才翻譯完成﹐不過因為 High Fidelity 和 About a Boy 兩部作品被拍成電影﹐他早就是當代英國作家裡出國比賽叫好叫座的寫手。從談論足球生活的 Fever Pitch﹐一邊聊愛情一邊聊音樂的 High Fidelity﹐到三十歲沒有經濟困擾、家庭壓力以致呈現社會真空狀態的 About a Boy﹐Hornby 的主角總是些看似輕鬆﹐想認真起來又極為混亂的老男孩。因為和大眾文化貼的很近﹐Hornby 的書往往配合著特定年代﹐和那個年代裡的某個典型。時間過去﹐這典型慢慢老了﹐心境還想繼續做聽音樂看足球的少年﹐社會卻一件一件貼上來﹐主角的苦惱越來越多﹐關心的事情也慢慢轉變﹐音樂和足球慢慢變成興趣﹐到本書則幾乎消失。
這本書特別的地方是觀點從男人變成了女人。女主角的職業是家庭醫生﹐做好所有社會認同的”好事“﹐丈夫是 SOHO 型的文字工作者﹐唯一穩定的收入來自社區報﹐每週一次在上面尖酸刻薄地大發牢騷。女主角時常希望丈夫變”好“﹐於是災難來臨﹕她的心願實現了。
此書仍然帶著極大的自傳(或是自省)風格﹐冷眼處理英國典型文化中產的生活。他們投給 Liberal﹐做資源回收﹐反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和貧窮。住在倫敦外圈的小房子﹐撫養子女﹐偶爾找保姆來看看孩子﹐去劇場區看戲。週末和朋友聚餐﹐一同諷刺看不過眼的政客、歌手﹐及所有他們看不起的人﹐確定彼此心照不宣﹐再心滿意足的回去。其典型和英國男人下班後一同去喝啤酒看球一樣經典﹐只是單位從“個人”變成了“家庭”。可能女性觀點畢竟是第一次使用﹐加上要自我反省總有些難堪意味﹐不似之前寫來這樣流暢。前面半本的大改變敘述完以後﹐後半像作者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只有亂七八糟草草了事﹐有點虎頭蛇尾。整本書除了一些戲謔的小段以外(列出他丈夫不喜歡的公眾人物就整整去了一頁)﹐最出色的是神來之筆的最後一段﹐描寫洪水殺進房子﹐父親爬上屋外清排水管﹐全家一起合作的片刻﹕
He's wearing jeans, and Tom and I grap hold of one back pocket each in an attempt to anchor him, while Molly in turn hangs on to us, purposelessly but sweetly. My family, I think, just that. And then, I can do this. I can live this life. I can, I can. It's the spark I want to cherish, a splutter of life in the flat battery; but just at the wrong moment I catch a glimpse of the night sky behind David, and I can see that there's nothing out there at all.
我和湯姆一人一邊抓著他牛仔褲後面的口袋﹐試著把他固定住﹐茉莉則在後面抓著我們﹐小手沒什麼實際作用但甜上心頭。我的家庭﹐我想﹐我的家。然後﹐我可以的。我可以這樣生活下去﹐我可以﹐我可以。我想珍惜這瞬間的火光﹐將盡電池的最後噴發﹔但就在這天殺時刻我瞥見大衛背後的夜空﹐那裡什麼也沒有。
Hornby 本身住在倫敦北郊﹐2001 年他編了一本書叫 Speaking with the Angel﹐所有收入捐給一所自閉兒特殊學校﹐他兒子就在那裡讀書。印象最深刻的是數火車 Transpotting 作者 Irvine Welsh 的短篇故事 Catholic Guilt﹐死去主人公的靈魂得到的處罰是“不斷夾進他人的性生活也就是不斷趴在受者身上被不斷地幹屁眼”﹕想到這裡或許我還是再去多看本 Welsh 。
2008/06/30
如何是好 How to be Good
訂閱:
張貼留言 (Atom)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