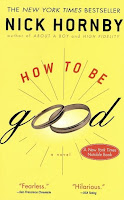故事很簡單﹕兩個個性迥異的美國女子 Vicky 和 Cristina 結伴到巴塞隆那旅行﹐遇上當地藝術家 Juan Antonio﹐同時被他吸引而捲入他和前妻 María Elena 的西班牙故事﹐再回到自己人生原軌。最後 Vicky 還是回到原本計劃好的婚姻生活﹐嫁給無聊樸實的 Doug﹐Cristina 仍然繼續她的不滿足。誰也沒改變誰﹐改變的只有認識自己無法改變。
旁白像慾望師奶 (Desperate housewifes)﹐電影配音裡那句重複的"Barcelona~" 單調無聊﹐但故事維持了 Woody Allen 凸顯荒謬的長項﹐諷刺的都很誠實。 南歐人的確覺得美國人直接、平板、缺乏熱情、毫無藝術素養﹐是只會用仿古傢具的“退化的歐洲品”。而世界上任何人到了南歐﹐剛開始都會驚訝地“找到自己”﹐但隨即發覺無法真正融入他們如神話神衹一樣混亂瘋狂﹐宿命到不可理喻的感情方式。
想和 Cruz 談戀愛嗎﹖偏偏自己又做不了 Javier Bardem。反之亦然。
Woody Allen 越老越勁﹐大概和老憤青 Mia Farrow 分手﹐順勢一次擺脫所有紐約知識份子的包袱有關。過去女主角那種神經質﹐知性卻不理性的典型總算被引人犯罪的性感取代﹐男主角們也紛紛有血(性)有(肌) 肉起來。就連 Match Point (2005) 裡唯一無法突破的激情戲都靠 Bardem 克服了( MP裡拿領帶朦眼睛那段簡直讓人誤會是笑點 - 這種事早點找專家不就好了嗎﹖)。
雖然 Woody 再離個幾次婚都成不了偶像 Bergman﹐但現在脫離 Manhattan 還不算太晚。



























.JPG)


.JPG)